《舟中曉望》鑒賞
原文
掛席東南望,青山水國遙。
舳艫爭利涉,來往接風潮。
問我今何適?天臺訪石橋。
坐看霞色曉,疑是赤城標。
賞析
孟浩然詩多寫自己的日常生活,常常“遇景入詠,不鉤奇抉異”(皮日休評價),故詩味的淡泊往往叫人可意會而不可言傳。這首《舟中曉望》,就記錄著他約在開元十五年自越州水程往游天臺山的旅況。實地登覽在大多數人看來要有奇趣得多,而他更樂于表現名山在可望而不可即時的旅途況味。
船在拂曉時揚帆出發,一天的旅途生活又開始了。“掛席東南望”,開篇就揭出“望”字,可見情切。詩人大約又一次領略了“時時引領望天末,何處青山是越中”的心情。“望”字是一篇的精神所在。此刻詩人似乎望見了什么,又似乎什么也沒望見,因為水程尚遠,況且天剛破曉。這一切意味都包含在“青山——水國——遙”這五個平常的字構成的詩句中。
既然如此,只好暫時忍耐些,抓緊趕路吧。第二聯寫水程,承前聯“水國遙”來。“爭利涉”以一個“爭”字表現出心情迫切、興致勃勃,而“來往接風潮”則以一個“接”字表現出一個常與波濤為伍的旅人的安定與愉悅感,跟上句相連,便有乘風破浪之勢。
到此自然想要知道他“何往”了,第三聯于是轉出一問一答來。這其實是詩人自問自答:這里遙應篇首“東南望”,點出天臺山,于是首聯何所望,次聯何所往,都得到解答。天臺山是東南名山,石橋尤為勝跡。這一聯初讀似口頭常語,無多少詩味。然而只要聯想到這些關于名山勝跡的奇妙傳說,就會體味到“天臺訪石橋”一句話中微帶興奮與夸耀的口吻,感到作者的陶醉和神往。而詩的意味就在無字處,在詩人出語時的神情風采之中。
正因為詩人是這樣陶然神往,眼前出現的一片霞光便引起他一個動人的猜想:在詩人的想象中,映紅天際的不是朝霞,而當是山石發出的異彩。這想象雖絢麗,然而語言省凈,表現樸質,沒有用一個精美的字面,體現了孟詩“當巧不巧”的特點。尾聯雖承“天臺”而來,卻又緊緊關合篇首。“坐看”照應“望”字,但表情有細微的差異。一般說,“望”比較著意,而且不一定能“見”,有張望尋求的意味。而“看”則比較隨意,與“見”字常常相聯,“坐看霞色曉”,是一種怡然欣賞的態度。可這里看的并不是“赤城”,只是詩人那么猜想罷了。如果說首句由“望”引起的懸念到此已了結,那么“疑”字顯然又引起新的懸念,使篇中無余字而篇外有余韻,寫出了旅途中對名山向往的心情,十分傳神。
此詩似乎信筆寫來,卻首尾銜接,承轉分明,篇法圓緊;它形象質樸,卻又真彩內映;它沒有警句煉字,卻有興味貫串全篇。從聲律角度看,此詩是五言律詩(平仄全合),然而通體散行,中兩聯不作駢偶。這當然與近體詩剛剛完成,去古未遠,聲律尚寬有關;同時未嘗不出于內容的要求。這樣,它既有音樂美,又灑脫自然。
孟浩然簡介
唐代·孟浩然的簡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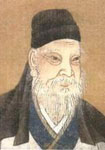
孟浩然(689-740),男,漢族,唐代詩人。本名不詳(一說名浩),字浩然,襄州襄陽(今湖北襄陽)人,世稱“孟襄陽”。浩然,少好節義,喜濟人患難,工于詩。年四十游京師,唐玄宗詔詠其詩,至“不才明主棄”之語,玄宗謂:“卿自不求仕,朕未嘗棄卿,奈何誣我?”因放還未仕,后隱居鹿門山,著詩二百余首。孟浩然與另一位山水田園詩人王維合稱為“王孟”。
...〔 〕